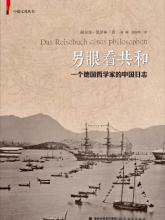关于本书
一位德国哲学家穿越半个中国,他会如何看待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中国社会;在旅途中,他如何结识清廷的遗老遗少,与国学大师辜鸿铭、学贯中西的大儒沈曾植产生深刻的友谊;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又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本书不仅影响当时欧美人士之亚洲文化观,也影响当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对于任何关心中西文化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必读书。
内容简介
《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成书于1919年,首版后即引起轰动。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埃及、锡兰、印度等,下卷包括中国、日本、美国等。在这本书中,凯泽林以较浓的笔墨叙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旅行经历及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即摘取了该书下卷第四章《远东行》之中国篇。适值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大致路径为香港-广州-澳门-青岛-山东其他城市-济南-北京-汉口-长江-上海,即由南至北,再由北至南,最后由上海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凯泽林初到中国,即感受到了弥漫中国的革命气息。作为出身贵族家庭的保守派人士,他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和共和制度的怀疑,以及对席卷世界的民主革命之风忧心忡忡。
纵观凯泽林的整个中国之行,也是他对中国哲学世界由浅入深、不断探索的过程。通过他的日记,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儒学的极度推崇,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通常是很高的,值得西方人学习。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过分讲求实际的民族性格以及“庸人之气”提出了批评,值得中国人反思。
凯泽林初到中国,即感受到了弥漫中国的革命气息。作为出身贵族家庭的保守派人士,他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和共和制度的怀疑,以及对席卷世界的民主革命之风忧心忡忡。
纵观凯泽林的整个中国之行,也是他对中国哲学世界由浅入深、不断探索的过程。通过他的日记,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儒学的极度推崇,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通常是很高的,值得西方人学习。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过分讲求实际的民族性格以及“庸人之气”提出了批评,值得中国人反思。
- 作者简介
- 媒体评论
目录
第一章:香港
第二章:广州
第三章:澳门
第四章:青岛
第五章:穿过山东
第六章:济南府
第七章:北京
第八章:汉口
第九章:长江之旅
第十章:上海
附录 北京八月
精彩节选
- 前言
赫尔曼·凯泽林(1880~1946),旧译盖沙令,德国社会哲学家。出生于爱沙尼亚的世袭伯爵家庭,祖父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顾问,祖母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财政大臣之女。从小在贵族环境下长大的凯泽林对其家世颇为自豪:“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俄国贵族”,称自己生来就具有“征服者和统治者的本性”。[1]
青年时代,凯泽林游学于欧洲各国,博览群书,及至触及豪斯顿·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开始矢志攻读哲学。他首创了一种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的松散哲学,兼采众家之长,化为己用。在他看来,哲学并非仅仅为了认知世界,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自身的完善。始于1911年的环球旅行是保成其形成松散哲学思想的重要契机。通过与各民族文化的直接接触和对话,凯泽林逐渐摈弃了欧洲学者惯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能够以平等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在此次旅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反映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其他著作包括《世界的结构》(1906年)、《不朽》(1907年)、《个性与时代精神》(1909年)、《自然哲学绪论》(1910年)、《德国真正的历史使命》(1919年)、《创造性的认识》(1912年)、《作为艺术的哲学》(1922年)等。1946年逝世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
《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成书于1919年,首版后即引起轰动。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埃及、锡兰、印度等,下卷包括中国、日本、美国等。1914年,凯泽林将书稿第一卷交付出版社付印,第二卷亦已完稿,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远居俄国的他无法与德国出版商取得联系,便将出版计划搁置。在一战进行的4年里,凯泽林在家潜心修改第二卷,几乎将其重写了一遍。因此,这部作品并不是单纯的旅游记录,借用凯泽林自己的话“与其说是游记,不如说是小说”。
在这本书中,凯泽林以较浓的笔墨叙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旅行经历及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游记》即摘取了该书下卷第四章《远东行》之中国篇。
凯泽林想象中国首先应当是一个充满伦理和道德、达到完美极致的理想国度。认为道义和礼仪是维持中国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力量,中国文化归根究底是一种伦理学或首先是实践哲学,中国人则是当今世界最高尚、最完美的民族。他对中国的美化和赞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建立了二元对立的模式,将中国作为人类精神和希望的代表,而西方则表现出了更多的物质性和颓废性。在他看来,中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而西方社会则已千疮百孔,非动大手术不可。
作为一个德国人,能够不顾一次大战之前德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大潮流和政治需求,也不顾德国灿烂的文化传统,而提出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要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他对东方文化和社会的推崇名过其实。倘若中国果真如凯泽林所言,历史上即不会有那么多次的改朝换代,也不会有近代史上的百余年屈辱了。
《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并非以传统的日记体裁撰写,所有章节均只根据旅行地点顺序粗略排序,并未标明具体日期,因此,我们只能推算出凯泽林到达中国的日期只能推算得出约1912年初,适值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大致路径为香港-广州-澳门-青岛-山东其他城市-济南-北京-汉口-长江-上海,即由南至北,再由北至南,最后由上海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凯泽林初到中国,即感受到了弥漫中国的革命气息。作为出身贵族家庭的保守派人士,他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和共和制度的怀疑,以及对席卷世界的民主革命之风忧心忡忡。在广州,作为一名精英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对充斥广东的商业氛围以及贫乏的精神生活深感失望。在青岛,通过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介绍,结识了许多清廷的遗老遗少,对他们在变革的漩涡中处世不惊深表赞赏。在北京,他结识了国学大师辜鸿铭,两人时常一起游览北京名胜,品尝佳肴,探讨中西哲学。在上海,经辜鸿铭介绍,结识了学贯中西的沈曾植,为其儒学大师的风范所倾迷。十余年后,凯泽林辗转寄给了沈曾植一张签名照,以作对当时会见的纪念,而此时距沈曾植离世已逾8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期间,凯泽林还于尚贤堂[2]作了此次中国之行的唯一一场公众演说,题为《东方与西方及其对共同真理之探索》,引起轰动。演说于1912年5月2日举行,俄国驻沪领事夫妇、法语学校教师、中国文学社团、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近百人参加。中国红十字协会副会长沈敦和主持讲座。凯泽林的演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西方哲学发展历程和面临的窘境,第二部分关注东方哲学特点,特别是与西方哲学互补之处,第三部分指出东西方哲学可以互学互鉴,也应成为中国今后发展方向。《大陆报》、《申报》、《共和日报》等媒体均予报道或转载,《尚贤堂纪事》还将演说稿全文译载并印成单行本发行。
纵观凯泽林的整个中国之行,也是他对中国哲学世界由浅入深、不断探索的过程。通过他的日记,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儒学的极度推崇,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通常是很高的,值得西方人学习。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过分讲求实际的民族性格以及“庸人之气”提出了批评,值得中国人反思。
秦俊峰
2014年4月25日
- 精彩书摘
第二章 广州
遗憾的是,我来到中国的时机很不合宜:整个国家正处在革命风暴的风口浪尖上。或许有人会将这一时刻称为“伟大的时代”,甚至有人还会为“曾经亲身经历过”而感慨终生;但对于远见卓识者而言,如此充斥着暴力变革的时代却是唯恐避之而不及。面对当前发生的诸多非同寻常的外部事件,绝大多数人失去了内心的宁静:他们人浮于世,完全不是原来的自己,对西方而言也不具有代表性;而一个真实的自己却被完完全全地遮掩了。试问:在那一段恐怖岁月或 “七月革命”[3]期间发生的暴力事件对于那些爱好和平的巴黎市民究竟有何意义?完全没有。他们只是群众运动中的演员,而且仅此角色而已。当然,也还是会有一些特例,只有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方能彰显英雄本色的“海燕”,它们“货真价实”,备受追捧,但数量却要远远少于人们的想象。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在特殊情况下的行为举止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的代表性。例如,几乎每一位绅士都会在危急关头展现勇气,几乎每一位母亲都会在她们的孩子遭到威胁时挺身而出。特别是在德国,当面临与职业相关的典型性危险时,如船长在轮船沉没时,将军在激烈的战场上,市长在他的城市遭受瘟疫侵袭之际,等等,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出色的表现证明自己的克尽职守,忠于使命。在这一时刻,这些被视为英雄的人物已不再是平日的自己,或是增添了许多陌生,或是仿佛换了个新人:他们不再作为个体而行动,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如此典型性的行动常常、甚至太过经常地带有一种与“本我”剥离的色彩,正如同断头台上的死刑犯在临刑前的滔滔不绝。当然,拿破仑却是与众不同的。他仅仅关注他的将军们在重要紧急关头的表现,但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总是要在最紧急关头做出决定,所以普通人在他而言可有可无;倘若拿破仑多多留意一些普通人的真实存在,或许他会做出另样的判断。当然,真实的存在不是必须在每天存在的范畴中体现出来,不需要像梅特林克[4]苦心积虑地百般维护,因为这样的一个范畴不是必须适应于每一个人。只有适宜的范畴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但此类范畴本质上却不应当是一种特例的状态。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长年太平盛世、秩序井然的国度!因此,我根本未曾认真严肃地看待过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革命运动。如果我不是大错特错的话,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未曾把这场革命当回事,至少在一个欧洲人看来如此。我得到的一种印象是,中国人对这场革命的看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所有曾经发生过的革命的看法别无二致:革命是生物机体的危机。在某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倘若不使用暴力,生物机体无法实现对这一阶段的逾越:机体会生病,会发热,会沸腾;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带有革命色彩的事件还不及一半);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毫无疑问乃是出自内部的需要,尽管革命带来的后果总体并不令人愉悦,对于法国尤甚;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旧制度[5]已经丧失了生命力,但却正是归因于旧制度的顽固不化,离开暴力的途径,别无他径可以将其打破。无论如何,此种不可避免的幼稚病并不能被视为英雄之举。因此,当我听到反复称颂“人民的英雄之举”时,不得不强忍笑颜。此种疯狂的状况在中国很难平息下来。不久之后,孙中山将不再被作为英雄人物而受到人们的敬重,人们或许对他从事的革命活动心存感激,但对其个人评价将会仅仅限于“一个温顺的、即便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理论家”。但是,倘若将孙中山置于欧洲,必然是一位响当当的“大英雄”。
我在中国的最初一段时间,不单单是时间上的不合宜,空间上亦是如此:在广州,生活的表象给人以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心理上似乎根本无法再透过表象而看清本质。如今,公众的生活对我而言已全无吸引力,因为它的形式无法表达出与其朝夕相处的灵魂所在,而仅能够体现相处的客观必然性或可能性。因此,单就此点而言,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交往,乃至人与动物的交往,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过去,人们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社会制度独特性的作品,但我却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社会制度并无显著差异;即便前者在事实上可能真的是独树一帜,但就内在意义而言,前者与后者的差别微乎其微。在如此一座因其独特的魅力而闻名于世的商业大都市里,我几乎从未有过身处异地的感受。(出于反证的目的)我不禁要问,一个形而上学的中国人在柏林或法兰克福又能够学到些什么?我想,在大都市的喧嚣中,他或许很难感受到此地与彼处在精神上的差异。他也许对勤奋和劳作要感受得少一些,而对不安和狂燥要感受得多一些,并很可能由此得出结论,即我们欧洲人与中国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文化层次上要低其一等。
为了不会一无所获,我暂时将形而上学者排除在外,而将一个纯粹的观察者请进上述的情景假设中来。广州或许是我所经历的城市中最为繁忙的一个,这里几乎没有游手好闲的懒汉。但是最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总是能够劳碌并快乐着。于是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欧洲人易于将中国人视作非人类。但凡将中国人与猴子相提并论的人,他们总要思考猴子有异于普通动物的独特之处,即在一张动物的脸上镶嵌着一双近似人类、闪烁睿智的大眼睛。因此,凡是长了一双大智大慧、生动流彩的眼睛的人,一定会流露出“猴精猴精”的神采,甚至诸如康德一样的伟人亦不例外。广州人只是看上去有些非人类,但没有给人一种动物的印象。尽管他们的生存状况在我们看来有损于人的尊严,但此种生存完全不是一种原生态,我们可以看到藏在深处的教育和文化的影子。因此,广州人的乐观精神是实实在在的文化产物。那么,这座城市又有哪些令人生厌之处?在我而言,委实难以提取不掺杂质的印象。首先,我不认为广州的肮脏和恶臭招人讨厌。与意大利的脏、臭不同,我却以为这恰恰是中国的独特风格,甚至是中国独具一格的魅力。譬如,我已渐渐习惯了贝拿勒斯[6]人身上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异味,甚至还有点喜欢上了这种味道。其次,我也不认为中国人令人厌恶。恰恰相反,中国人总能够给外国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我看来,或许是浓厚的铜臭味和商业气息使得这座城市令人反感。只要我与中国的小生意人相处时间长久,总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但仅此一点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思来想去,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广州最令我厌恶的是机械式的、失却灵魂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这座城市里毫无目的地劳作着,在他们的身上根本无法找出生意人应当具备的最主要的特征,即大视野下的商业活动。他们只会像勤劳的蚂蚁一般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但如果这些“蚁族”——他们充其量也就是群“蚂蚁”——带着一幅充满睿智的面孔,而且毫无疑问地受过良好教育,这就显得有些令人可怕了。
[1] 梁凌益:《盖沙令到中国来干什么?》,载《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5期,第18页。
[2] 由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于1897年在华创办和经营的书报出版机构,初设北京,1903年迁往上海。建成后设立学校,定期开放堂舍接纳参观,并举行专题演讲报告会,很快成为近代上海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之一,许多名人演讲、集会、展览,甚至社会名流的追悼会均在此举行。
[3] 1830年7月,法国推翻复辟波旁王朝,拥戴路易-菲利浦登上王位的革命。建立的新王朝被称为“七月王朝”。“七月革命”是1830年欧洲革命浪潮的序曲。
[4]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哲学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象征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青鸟》、《盲人》、《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蒙娜·凡娜》等。早期作品充满悲观颓废的色彩,宣扬死亡和命运的无常,后期作品研究人生和生命的奥秘,思索道德的价值,取得很大成功。
[5] 特指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
[6] 贝拿勒斯(Benares),瓦拉纳西(Varanais)的旧称,印度教圣地,位于印度北方邦东南部恒河中游。
其它信息
开 本:16开